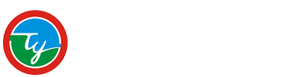谁给我儿子一块踢球的绿地?
时间:2011-11-17 21:44:25 来源: 作者:
儿子今年9岁。也许是因为老爸我是一个体育记者缘故,也许是2008年奥运会亲临现场看了两次比赛,那一年他6岁,突然喜欢上了体育,直至今日,堪称酷爱。疯狂的爱好
自打他喜欢上体育后,只要坐在电视机前,频道基本锁定在CCTV5;一般情况下,家里晚饭都是18时准时开始,没有任何其他原因,就是因为那个点有一档体育新闻,只有看着这个节目,他才能很好地吃饭。每天只要到这个点,即便手头作业再多,即便面临期中期末考试,他也要坚持收看这档体育新闻。
自然,和大多数喜欢体育的人一样,足球和篮球是儿子的最爱。南非世界杯时,因为时差,大多数比赛他都无法看直播,但只要能看的,他都坚持看,实在看不到的,第二天起大早看新闻。小组赛结束后,他甚至自己在家里的小黑板上画出淘汰赛的对阵表,赛前一天将自己猜的比分用蓝色粉笔写在旁边,比赛结束后将双方真实结果用白色粉笔写出来,两相对照。我至今记得,8进4的四场比赛,他竟然猜对了三场,不止是胜负结果,比分也完全吻合。当然,我从来没有认为儿子是个天才,只是瞎猫逮着死耗子了。记得当时他和我的一个朋友讨论荷兰和巴西那场比赛,对于两队的主力阵容、每个队员什么位置差不多是脱口而出,尤其是他说出荷兰队范布隆克霍斯特这个名字时,我的那个朋友顿时折服,我这个还算懂点球的朋友,曾经特意记过几次,但怎么也记不住这个读起来十分拗口的名字。差不多是从一年级下半学期,他还不到7岁时,开始迷上NBA,一发不可收拾。每天放学接他回家时,他的第一个问题一定是今天谁对谁的比分是多少。有一段时间,在完成学校作业后,他几乎总是抱着《篮球先锋报》编撰的《NBA终极兵书》在研究,当时几乎NBA一线球星的身高、场上位置、赛季数据,他差不多都能脱口而出。全明星赛前,他会自己在纸上排出一个他心目中的东西部明星队。二年级的一个期末,班要搞学生特长的自我展示,儿子选择了为班级同学讲NBA,为此,还专门和他所崇拜的《篮球先锋报》总编辑苏群通了电话,以求证相关资料和信息。偶尔我带他到办公室,他会直接窜到对面的《篮球先锋报》编辑部,和那里年轻的编辑记者们讨论NBA赛事。今年NBA到现在还在停摆,儿子显得很失落也很无奈,经常对我唠叨一句话:“球员和老板每年都挣那么多钱,怎么就因为这百分之几点几的利益互不相让呢?”不过他说,好在CBA就要开始了。
儿子的兴趣绝不仅限于足球和篮球,最近的女排世界杯,举重世锦赛,此前的全运会、亚运会,甚至残奥会,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关注。记得冰壶世锦赛时,正好是寒假,只要有直播,他就会饶有兴趣地收看。我很纳闷,这样的比赛我是不会看,也看不懂,然而儿子却一五一十地将冰壶比赛的规则讲给我,俨然给我这个体育记者当起了老师。
践行的无奈
儿子喜欢体育,绝不是那种“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是亲身参与的热情极高。通常情况下,只要提出带他或者让他和楼上的小朋友一起踢足球、打篮球、打羽毛球乒乓球等等,他都会以极高的热情参与。即便是他完成繁重功课作业后极度疲惫,也无法阻挡他参与一项体育活动的热情,而且参与后那种对天性和野性释放给他带来的快感,也是让他完成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看到的一种表情。
但是,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处处被商业大潮笼罩的城市生活,给儿子的体育践行,又带来了很多的无奈。
我家住在北京的方庄。方庄是一个怎样的社区,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人都清楚,高楼林立、人口密度极大,空间极度压抑。谢天谢地,政府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还为社区居民建了一个体育公园。有一块标准足球场,还有室内外网球场、羽毛球馆、室外灯光篮球场等等,站在我家窗户上,即可看到每一片场地上热火朝天地锻炼着的人们。我以为这样的便利会给喜欢体育的儿子带来很多机会和快乐。然而第一次,我们就吃了闭门羹。当我抱着足球带着儿子准备进足球场时,被拒绝了。我知道那是收费的,无论多大孩子都得缴费,而且为了利益最大化,将一个标准足球场分为四五个小场地,每天都有人鏖战到夜里十点多。门卫告诉我,孩子太小,没有专门为他这么大孩子的场地,那么多大人在踢,孩子的安全无法保证,即便家长带着也不行。就此,三年多了,我一直劝告儿子,不要有进去的念想了。
经常去国外采访,尤其在欧洲,随处可见城市里一块块免费开放的绿地,和三五成群如儿子般大小的孩子们,在草地上嬉戏打闹追逐着足球,然后看着儿子趴在铁丝网上看着方庄体育公园里那些大人们挥汗如雨,就觉得如儿子这般年龄的北京的孩子们真的可怜,失去了那么多快乐。
那就改打篮球吧。去年的时候,体育公园内的篮球场一人一小时5元,但被告知,像他这么大的孩子只能由家长陪伴才能入场,自然要买两个人的门票,而且,为了孩子安全,人多时就别进去了。十块钱两个人锻炼一小时,内心的感觉有点幸福,但今年门票一下涨到只要入场一人12元,像他这么小的孩子,也没有任何优惠。即便如此,只要空间和时间允许,我都会带着儿子进去玩一会的。尽管以他的身高和力量,要将篮球投进框里很费劲,12块钱对他来说稍有浪费之嫌,但当他将篮球晃晃悠悠地扔进篮筐一次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兴奋和成就感,作为家长的我自然不会在乎12块钱了。有一次,在球场上碰见了足协的新闻官董华,他也是带着儿子来的,聊起孩子们的体育活动,他和我有着同样的无奈。离体育如此近的中国体育官员和体育记者,尚有如此无奈呀!
很幸运,篮球场场东侧还有很大一块水泥板铺就的空地,那些不愿意花钱或者进不去场地的人,就三五成群地在此地“野战”。尽管时有遛狗者和他们的小狗闯入,也无法阻挡野战者得热情。我和儿子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两块砖头当球门,经常为一个球进还是没进争得面红耳赤,儿子的腿也经常因为摔在水泥地上而青一块紫一块,那也会疼并继续着。
但好景不长,好地儿不常有。从今年夏天,这块空着的水泥地被圈起来了,立起了一个营业性质的儿童充气城堡,尽管因为夏天暴晒、冬天寒冷,没有几个孩子会进来“充气”,但这个城堡依然屹立不倒,儿子每每经过这儿时,都要嘟囔两句,表达自己失去了这块阵地的不满。
据说方庄体育公园是用体育彩票公益金建起来的,平时的维护、保养都靠体彩基金,不知谁这么胆儿大,把这块空旷的水泥地给出租了?
这就是生活在方庄的孩子的现实,看似离体育场很近,但离体育活动却那么远。而那些生活在周边连一个体育公园都没有的社区的孩子们呢?在北京,如方庄这样有一个体育公园的大社区凤毛麟角。
缺失的学校体育生活
儿子的小学离中国足协办公的东玖大厦很近,坐落在中国体育的中枢神经区域。是一所市级重点小学,也是一所有着浓厚体育传统的学校。
当中国足协的 “校园足球计划”轰轰烈烈地开展之时,我当时“很自私”地想,离中国足协如此近,而且和国家体育总局有过较好合作的这个学校一定会被选为试点,果真如此,儿子和他的那些喜欢踢球的同学就该幸福了,课余时间可以有很多时间踢球,还配有专门的辅导老师。但事与愿违,他们的学校并没有被选中。我一直想不明白,如此近距离方便足协校园足球领导组视察、监督、辅导,为什么没被选中呢?离足协如此近,却离校园足球那么远。后来听说了很多关于校园足球的事:比如,很多小学希望踢球的孩子越少越好,校园足球最好别选中他们学校做试点,因为会带来很多麻烦,影响到学校正好教学计划,还可能因孩子受伤而承担责任;再比如,有些被选中的,在争取到一定经费和训练装备后,并不按照校园足球计划开展活动,只是有人检查的时候,组织一拨学生“声势浩大”地在操场上踢踢;再比如,有人说校园足球理应由教育部门主导,一些小学只听自己上级领导的话,足协凭什么要对学校提要求等等。鉴于此,一些学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足协在选择试点学校时,也不完全具有主动权。
好在儿子学校还有课后兴趣班,在种类繁多的科目中,儿子毫不犹豫选择了足球。尽管是收费的,尽管我知道学校体育老师带的这样的兴趣班,只能被称作“替家长多看一个小时孩子”,但同样毫不犹豫地支持儿子的选择。据说,选择报足球班的孩子很多,由于场地和名额有限,体育老师只能根据报名先后取舍,儿子由于积极,报名靠前,被选中了,和他一样幸运的还有近20个孩子。
每次足球课我都会提前一点时间去接他,隔着学校大门的栅栏看着,这些年龄大小不一、个头参差不齐的孩子那样投入地完成每一次并不太规范的动作,尤其是分队比赛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每球必争,摔倒了爬起来接着来,一点也看不出社会上所谓的独生子女骄娇之气。回家的路上,儿子还会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足球课上趣事,言语间充满了满足感。有两三次,儿子因为被踢伤或摔伤,是一瘸一拐地走出校门的,作为家长的我并没因此而心疼,反而因为儿子的一脸的满足而内心高兴。我想,如儿子一样状况的绝不是儿子一人,而和我有同样想法的家长,也绝不是我一人。
就这样一连参加了三个学期的足球班。今年,因为学校改造,在原本就狭小的操场上盖起了一排房子,足球课后班没有,原先矗立在操场上的4个篮球架也没了,而且这个学期的课后兴趣班竟然没有任何一项和体育相关的科目了。为此,儿子急得几